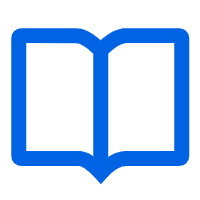静姝的孩子是谁的?
《诗经》的第一篇是《关雎》,最后一篇是《静姝》,一开一合皆是男子思念女子的故事。《关雎》中,那“参差荇菜”的河畔,一位窈窕淑女撩拨了男子的心弦。
“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,辗转反侧。……”他想她,他追求她,他思慕她,他梦想与她琴瑟在御,钟鼓乐之。可那是一厢情愿,并没有下文。《静姝》似乎要给出答案,一开头就点明了结果:两人好上了,“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……静女其娈,贻我彤管”。
诗中女子不仅长得美,还颇有心机,故意迟到,让前来赴会的男友焦急万分;还“贻我彤管”,你侬我侬,爱意绵绵。这故事听起来是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,而且这静姝对“我”的情致和态度,连带着对“我”的身体,都是欣赏、爱惜的,不是那种下贱、放纵的女人。“彤管”是乐器,“洵美且异”,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精致的琴。
《静女》
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。
静女其娈,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,说怿女美。
自牧归荑,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,美人之贻。
《静女》一诗,向来为选家所注目。现代学者一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恰当地评价其特点,认为它“风格朴素优美,给读者展示了一幅萧伯纳所说的那种‘第一交际’的动人画卷”(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),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;而古代的诗学家则把它作为 erotica来读。
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静女》,刺时也。卫君无道,夫人失位,故陈静女幽思之诗以风焉。一说,淫奔也。”其实在先秦时代,男女自由相会的例子是很多的,《郑风·将仲子》中的姑娘是这样,《召南·野有死麕》中的姑娘也是这样。姑娘们的羞涩、热情与机智,通过诗的语言不胫而走。在《邶风·静女》中,一位“俟我于城隅”的姑娘,在与她的情郎“爱而不见”的时候,是多么俏皮,多么有情致,她悄悄地躲藏了起来,以致她的“搔首踟蹰”的傻愣愣的情郎不见她,急得抓耳挠腮。
她赠送给情郎那“彤管”和“洵美且异”的“荑”,使她的情郎“说怿”异常,欣喜之至。诗中的男女“静女”与“我”(小伙子)的幽会,是那样的真诚,那样的温馨,令人羡慕不已,爱不释手。在“后妃之德”、“夫人之德”的礼教压制和“男女授受不亲,嫂叔不通问”之类的清规戒律的强制下,诗中的女主人公“静姝”简直是一种异样的女英雄,让人肃然起敬,情不自禁地为她称快。
郑笺说“女蒙恶邪,故匿而不见”,“蒙恶”云云,完全是以成人的眼光和大人的意志来约束男女青年的“无邪”和“非礼”。朱熹《诗集传》又说“此淫奔期会之诗”,更是视《静女》为洪水猛兽,大肆挞伐。